鉴赏
此为七夕词。作者记述的是七夕夜触景生情,伤心怀人之事。
上片起首三句,写七夕所见天空景象,并及七夕传说。七夕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节日,《艺文类聚》卷四中有七夕天上牛女相会和民间乞巧习俗的早期记载。至于牵牛、织女星分隔天河东西,只准每年七夕相会一次,传说就更早,后来又发展为乌鹊填桥之说。七夕这一晚,当阴历七月的上旬,月相为上弦,其状如弓,光线本来就不太亮,当云彩遮蔽时,从地上望去,就更显得朦朦胧胧,而星光也就显得暗淡了,故曰“月胧星淡”。这时候,作者想起了今夕是双星渡河之夕,于是便写出了“南飞乌鹊,暗数秋期天上”两句,以咏其事。“月胧星淡”正是最好的相会环境。这几句,叙事、写景之外,还蕴含着对牛女相会的歆羡、赞美之意。
上片歇拍句,写自己此佳节中的情况。“锦楼”句是说没有庆节摆设。《东京梦华录。七夕》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可见到了宋代,七夕已成为一个相当热闹的节日,庆节摆设是繁多的。“锦楼”即“彩楼”,总指节日铺陈。作者是个山野隐士,他不作此种铺陈,故曰“彩楼不到野人家”。眼前所对的,仅“门外清流叠嶂”而已。此句大有深意。我们知道,七夕这天,年轻妇女结彩缕穿针,向织女乞求心灵手巧了,恩爱夫妻向此对象征永恒爱情的神仙盟誓,祈求爱情的进一步净化与持久。而作者独对“清流叠嶂”而不结“锦楼”乞巧,则充分透露出作者心情的枯槁孤寂,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以此作结,为下片带来抒情叙事的文阔余地。
过片紧承前文,进一步敞示心灵的创痛。“一杯相属”三句,以沉痛的询问,抒发出丧失伴侣的悲哀。“一杯相属”,常有的表现。“佳人何?不见绕梁清唱”,这是痛苦的呼喊:劝我以美酒、娱我以清歌的佳人不了。——其中包括多少对前尘往事的追忆,对今日形单影只的伤心!从“绕梁清唱”句可看出,作者失去的那位“佳人”,本是一位歌女。词写至此,作者为什么不结彩楼以庆七夕,已得到了充分的解答,很好地呼应了前文结尾二句,以天上爱情的美满反衬人间爱情的不幸,返回牛女事作结。“人间平地亦崎岖”,同天上的牛郎、织女相比,有着多么大的差距!于是,作者最后唱出一句:“叹银汉何曾风浪!”银河里是不起风浪的,牛女的爱情,亘千万亿年以至永恒,不衰不灭。这是有力的反衬,弥觉人间的不美满,骨子里是突出作者自己的不幸。这一结束,议论而兼抒情,接触到一个普遍性、永恒性的感慨,耐人寻味。从结构上来说,它回应了开头,紧扣七夕话题,使全词显得圆融、完整。
这首词把眼前景、心内情,仙凡恋、男嫒巧妙地揉合一起。起承转合一起。起承转合,流畅天间,当为佳作。
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赏析
这首词是一首咏七夕的词作,但是,全篇却没有谈什么男女伤别、儿女恩爱,而是以天上、人间的对比,描绘了人间的不平,抒写出世路的艰险。这是有感于北宋王朝末期衰败的局势,而发出的感叹。
上片写天上。“月”、“星”、“乌鹊”、“秋期”、“锦楼”,均为天上景物。锦楼,相传为汉武帝的曝衣楼,在太液池西面,每年七月七日,宫女出来曝晒后宫衣物(见《西京杂记》)。秋期,即七夕。相传农历七月七日夜间,牵牛、织女过鹊桥,相会于银河东侧,是为秋期(见《尔雅翼》)。在列举了这些天上美妙、令人神驰心往的景物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写道:“锦楼不到野人家,但门外、清流叠嶂。”挺拔高奇,为戛然独造之境。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是宫阙锦楼,一个是“清流”、“叠嶂”的“野人家”。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下片,写人间。一开始,即发出“一杯相属,佳人何在?不见绕梁清唱”的叹谓。相属,即敬酒、祝酒,祝、属相通。绕梁清唱,形容歌声的美妙。典出《列子汤问》:韩娥过雍门,唱歌求食。走后,余单音间绕梁,三日不绝。后来,人们用以形容美妙动人的歌声或歌者。这里指“佳人”。结尾写道:“人间平地亦崎岖,叹银河、何曾风浪。”直言不讳,一语道破了作者写词的意图。从而,成为千古名句!
我国古典诗词中,咏七夕的作品不少,唐杜牧的《秋夕》,就是著名的一首。全诗只有四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写的是宫女的忧思怨绪。诗中却不着一字,而是通过清冷的画面,和诗人“轻描淡写”表现出来,于含蓄的景物描写之中见“精神”。
而这首七夕词,写的天上宫阙和人间村荒野户的形象对比。而且通过对比,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慨叹。别是一番立意和独特构思!“人间平地亦崎岖,”这振荡时代的强音,发自一个封建时代的词家之口,实是难能可贵!
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谢薖(kē)(1074~1116)字幼盘,自号竹友居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诗人,江西诗派二十五法嗣之一。谢逸从弟,与兄齐名,同学于吕希哲,并称“临川二谢”。与饶节、汪革、谢逸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一枝花〕
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
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蹅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鑞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城十二楼前步,远腾腾似入蓬莱路。
【滚绣球】红冉冉绿依依花笼阴映玉除,清浅浅响溅溅水流香出翠渠,明朗
朗墨浸浸八龙篆太霞深处,宽绰绰静绕雕栏依翠槛展转盘纡。滑擦擦细粼粼
布金沙云阶武夫,轻厮琅琅隔琳窗霞绡响佩琚,薄设设净匀匀蒙画栏
银屏水涵云母,齐臻臻滴溜溜挂珠箔卷绣帘钩搭珊瑚。香霭霭暖溶溶树缥渺迷青
琐,气森森光闪闪金屋棱层绚碧虚,真乃是人间天上全殊。
【倘秀才】萧爽似瀛海东扶桑奥区,廓落似阆苑西蟠桃圣圃。一片天光浸玉
壶,阁门珠路Λ。复道锦氍毹,上青华洞府。
【脱布衫】丹青绘绛阙清都,奎星灿宝检灵书。龙虎卫飞天象符,风霆护太
玄琼录。
【醉太平】以琴书自娱,与道德为徒。孔情周思乃畲,摆列着牙签玉轴。
上青冥借嫦娥八窍月中兔,采神芝倩麻姑七宝山前鹿,访丹丘赁张公千岁杖头驴,
乐逍遥分福。
【尾声】近北轩竹摇烟毵毵凤展冲霄羽,对南楼松挂月矫矫龙衔照乘珠。绰
约仙君溢莅广居,玄默无为道味腴。一寸心存太古初,万里神游广漠墟。萼绿飞
琼时寄语,赤鲤青鸾频报覆。报覆道沧海碧云拱望舒,恁时节鹤驭云降王母。 元日朝贺
一声莺报上林春,五更鸡唱扶桑晓。贺三阳万国来朝,践天街车马知多少,
端的便塞满东华道。
【滚绣球】赤羽旗疏刺剌风尚高,丹墀陛湿浸浸雪未消,金銮殿淡氤氲瑞烟
缭绕,玉狮炉香馥馥兰麝风飘。银酥蜡明灿灿金莲护绛绡,采鸾扇微影影青鸾纛
翠翘,氍毹锦软茸茸平铺着宝街复道,珊瑚钩滴滴溜高簇起绣幕珠箔。九龙车霞
光闪闪明芝盖,五凤楼日色瞳瞳映赭袍,隐隐鸣鞘。
【倘秀才】鹭班文僚武僚,熊虎队龙韬豹韬,八府三司共六曹。象牙牌犀
角带,龟背凯雁翎刀,有丹青怎描?
【脱布衫】椒花颂万代歌谣,柏叶杯九酝葡萄。茵陈簇雕盘翠缕,金花插玳
筵宫帽。
【小梁州】一派仙音奏九韶,端的是锦瑟鸾箫。红牙象板紫檀槽,中和调,
天上乐逍遥。
【幺篇】瑶池青鸟传音耗,说神仙飞下丹霄。一个个跨紫鸾,一个个骑黄鹤,
齐歌齐笑,共王母宴蟠桃。
【尾声】麒麟来三岛,蛮貊貔貅静四郊。刁斗无惊夜不敲,露布无文送
青鸟。弼辅移承尽所学,虹气夔龙不惮劳。端拱无为记舜尧,祝寿年年拜天表。 题梧月堂
向朝阳春长凤枝新,拂青霄根托龙门盛,覆高堂苍玉亭亭。素华朱户相辉映,
占人间一片清虚境。
【滚绣球】青蔼蔼参差绕翠楹,光朗朗玲珑透碧棂,密匝匝护浓阴玉池金井,
轻拂拂荡微风幽韵繁声。高耸仓蔚蓝天画不成,宽绰绰广寒宫夜不扃扃,滴溜溜
挂雕檐一轮宝镜,明闪闪映珠箔万叶光晶。舞翩翩九苞迷青琐,娇滴滴半夜
嫦娥下紫清,万种幽情。
【倘秀才】银床净缤纷落英,碧天朗扶疏弄晴,夜色秋光一样明。绕枝乌不
定,捣药兔长生,尘居的自省。
【脱布衫】肃金茎白露泠泠,金炉香雾冥冥。近雕甍珠星浅淡,揭朱帘玉
河澄映。
【小梁州】虚敞似瑶台十二层,满目空清。金精光射玉壶冰,轩窗静,何用
九枝灯。
【幺篇】一襟潇洒多情兴,久已后蜕骨超形。漏渐残,人初静,雕栏独凭,
挥手唤长庚。
【随煞尾】休言五柳夸幽胜,未羡三槐播令名。自是高人乐意萦,衿带仙家
白玉京。无竹无丝乱视听,逸典奇书自幽咏。料得无因驻清景,栖息盘桓不暂停,
不由人踏破琼瑶半阶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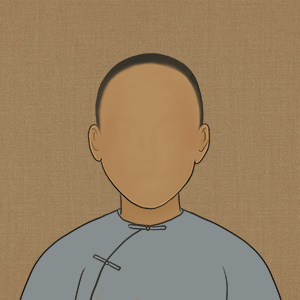 谢薖
谢薖 白居易
白居易 韩愈
韩愈 关汉卿
关汉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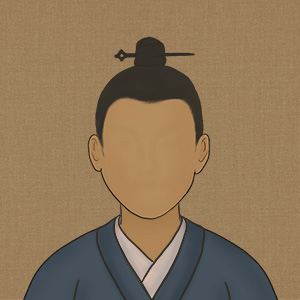 汤舜民
汤舜民 王恽
王恽 张抡
张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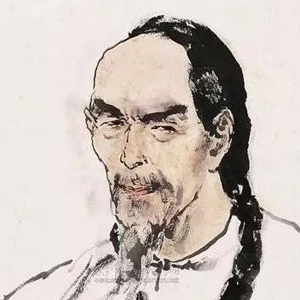 龚自珍
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