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丈夫死于战乱她独守茅屋受煎熬,身穿苎麻布衣衫鬓发干涩又枯焦。
桑树柘树全废毁仍然还要交纳蚕丝税,田园耕地已荒芜仍要征收农业税。
时常在外挖些野菜连着根须一起煮,现砍生柴带着叶子一起烧。
任凭你住在比深山更深的偏僻处,也没办法逃脱官府的赋税和兵徭。
注释
蓬茅:茅草盖的房子。
麻苎(zhù):即苎麻。鬓发焦:因吃不饱,身体缺乏营养而头发变成枯黄色。
柘:树木名,叶子可以喂蚕。征苗:征收农业税。
后:一作“尽”。
和:带着,连。
旋:同“现”。斫:砍。生柴: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湿柴。
征徭:赋税和徭役。
参考资料:
鉴赏
此诗反映了在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全诗通过山中寡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悲惨命运,透视当时社会的面貌,语极沉郁悲愤。诗人把寡妇的苦难写到了极至,造成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从而使人民的苦痛,诗人的情感,都通过生活场景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产生了感人的艺术力量。
此诗的“夫因兵死守蓬茅”,就从这兵荒马乱的时代着笔,概括地写出了这位农家妇女的不幸遭遇:战乱夺走了她的丈夫,迫使她孤苦一人,逃入深山破茅屋中栖身。
“麻苎衣衫鬓发焦”一句,抓住“衣衫”、“鬓发”这些最能揭示人物本质的细节特征,简洁而生动地刻画出寡妇那贫困痛苦的形象:身着粗糙的麻布衣服,鬓发枯黄,面容憔悴,肖其貌而传其神。从下文“时挑野菜”、“旋斫生柴”的描写来看,山中寡妇应该还是青壮年妇女,照说她的鬓发色泽该是好看的,但由于苦难的熬,使她鬓发早已焦黄枯槁,显得苍老了。简洁的肖像描写,衬托出人物的内心痛苦,写出了她那饱经忧患的身世。
然而,对这样一个孤苦可怜的寡妇,统治阶级也并不放过对她的榨取,而且手段是那样残忍:“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此处的“纳税”,指缴纳丝税;“征苗”,指征收青苗税,这是代宗广德二年开始增设的田赋附加税,因在粮食未成熟前征收,故称。古时以农桑为本,由于战争的破坏,桑林伐尽了,田园荒芜了,而官府却不顾人民的死活,照旧逼税和“征苗”。残酷的赋税剥削,使这位孤苦贫穷的寡妇无以为生。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只见她不时地挖来野菜,连菜根一起煮了吃;平时烧柴也很困难,燃生柴还要“带叶烧”。这两句是采用一种加倍强调的说法,通过这种艺术强调,渲染了山中寡妇那难以想象的困苦状况。最后,诗人面对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发出深沉的感慨:“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深山有毒蛇猛兽,对人的威胁很大。寡妇不堪忍受苛敛重赋的压榨,迫不得已逃入深山。然而,剥削的魔爪是无孔不入的,即使逃到“深山更深处”,也难以逃脱赋税和徭役的罗网。“任是”、“也应”两个关联词用得极好。可以看出,诗人的笔触象匕首一样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
诗歌是缘情而发,以感情来拨动读者心弦的。《山中寡妇》之所以感人,正在于它富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但诗并不直接抒情,而是把感情诉诸对人物命运的刻画描写之中。
诗人把寡妇的苦难写到了极至,造成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从而使人民的苦痛,诗人的情感,都通过生活场景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产生了感人的艺术力量。最后,诗又在形象描写的基础上引发感慨,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一个更广阔的境界,不但使人看到了一个山中寡妇的苦难,而且使人想象到和寡妇同命运的更多人的苦难。这就从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揭露了残酷的剥削,深化了主题,使诗的蕴意更加深厚。
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参考资料:
杜荀鹤(846~904),唐代诗人。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汉族,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大顺进士,以诗名,自成一家,尤长于宫词。大顺二年,第一人擢第,复还旧山。宣州田頵遣至汴通好,朱全忠厚遇之,表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天祐初卒。自序其文为《唐风集》十卷,今编诗三卷。事迹见孙光宪《北梦琐言》、何光远《鉴诫录》、《旧五代史·梁书》本传、《唐诗纪事》及《唐才子传》。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尚得自举判官,无间于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愈再拜。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去也。 托咏
剔秃一轮天外月,拜了低低说:是必常团圆,休着些儿缺,愿天下有情底
都似你者!
 杜荀鹤
杜荀鹤 韩愈
韩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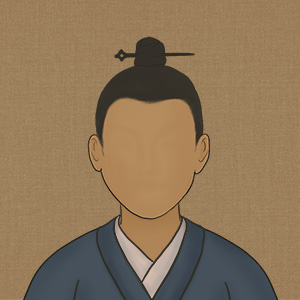 宋方壶
宋方壶 张可久
张可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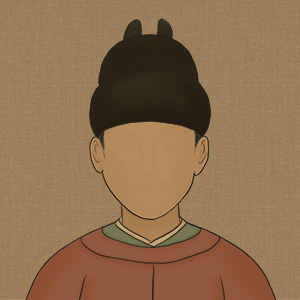 顾夐
顾夐 徐有贞
徐有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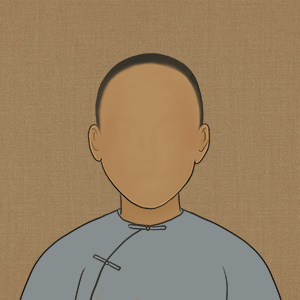 刘镇
刘镇 毛奇龄
毛奇龄 朱孝臧
朱孝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