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沅江湘江长流不尽,屈原悲愤似水深沉。
暮色茫茫,秋风骤起江面,吹进枫林,听的满耳萧萧。
注释
三闾(lǘ)庙:即屈原庙,因屈原曾任三闾大夫而得名,在今湖南汨罗县境。
沅(yuán)湘:指沅江和湘江,沅江、湘江是湖南的两条主要河流。
屈子怨何深:此处用比喻,屈子指屈原,句意屈原的怨恨好似沅(yuán)江湘江深沉的河水一样。何深:多么地深。
“日暮”二句:此处化用屈原的《九歌》《招魂》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秋烟:一作“秋风”。萧萧:风吹树木发出的响声。
参考资料:
鉴赏一
这是作者游屈原庙的题诗。此诗题一作《过三闾庙》,是诗人大历(766-779)中在湖南做官期间路过三闾庙时所作。伟大诗人屈原毕生忠贞正直。满腔忧国忧民之心,一身匡时济世之才,却因奸邪谗毁不得进用,最终流放江潭,遗恨波涛。他的峻洁的人格和不幸遭遇,引起了后人无限的景仰与同情。在汉代,贾谊、司马迁过汨罗江就曾驻揖凭吊,洒一掬英雄泪。贾谊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而司马迁则在他那“无韵之《离骚》”(《史记》)里写了一篇满含悲愤的《屈原列传》。时隔千载,诗人戴叔伦也感受到了与贾谊、司马迁同样的情怀:“昔人从逝水,有客吊秋风。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湘中怀古》)大历年间,奸臣元载当道,嫉贤妒能,排斥异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诗人来往于沅湘之上面对秋风萧瑟之景,不由他不动怀古吊屈的幽情。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作者谒庙,感慨颇深,《题三闾大夫庙》就是作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景成章的。
诗的前二句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沅湘流不尽”发语高亢。如天外奇石陡然而落,紧接着次句“屈子怨何深”又如古钟震鸣,沉重而浑厚,两句一开一阖,顿时给读者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从字面上看,“沅湘”一句是说江水长流,无穷无尽,意思当句自足。但实际上“流”这里是双关,既指水同时也逗出下句的“怨”,意谓屈子的哀愁是何等深重,沅湘两江之水千百年来汩汩流去,也流淌不尽、冲刷不尽。这样一来,屈原的悲剧就被赋予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意义。诗人那不被理解、信任的悲哀,遭谗见谪的愤慨和不得施展抱负的不平,仿佛都化作一股怨气弥漫在天地间,沉积在流水中,浪淘不尽.作者在这里以大胆的想象伴随饱含感情的笔调,表现了屈原的哀怨的深重,言外洋溢着无限悲慨。“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以沅水湘水流了千年也流不尽,来比喻屈原的幽怨之深,构思妙绝。屈原与楚王同宗,想到祖宗创业艰难,好不容易建立起强大的楚国,可是子孙昏庸无能,不能守业,贤能疏远,奸佞当权,自己空有一套正确的治国主张却不被采纳,反而遭到打击迫害,屡贬荒地。眼看世道,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朝政日非,国势岌岌可危,人民的灾难越来越深重,屈原奋而自沉汨罗江,他生而有怨,死亦有怨,这样的怨,没有个尽头。这二句是抒情。
后二句写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秋风萧瑟,景象凄凉,一片惨淡气氛,诗人融情入景,使读者不禁慨然以思,含蓄蕴藉地表达了一种感慨不已、哀思无限的凭吊怀念之情。这两句暗用《楚辞·招魂》语:“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但化用得非常巧妙,使人全然不觉。诗的后两句轻轻宕开,既不咏屈原的事,也不写屈原庙,却由虚转实,描绘了一幅秋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这并不是闲笔,它让读者想到屈原笔下的秋风和枫树,“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招魂》)。这是屈原曾经行吟的地方。朱熹说“(枫)玉霜后叶丹可爱,故骚人多称之”(《楚辞集注》)。此刻骚人已去,只有他曾歌咏的枫还在,当黄昏的秋风吹起时,如火的红枫婆娑摇曳,萧萧絮响,像在诉说千古悲剧。
这首诗比兴手法相当高明。前二句以江水之流不尽来比喻人之怨无穷,堪称妙绝。后二句萧瑟秋景的描写,又从《招魂》“湛湛江水”两句生发而来,景物依稀,气氛愁惨,更增凄惋,使人不胜惆怅,吊古之意极深,为人传诵。
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展开阅读全文 ∨
鉴赏三
司马迁论屈原时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史记·屈原列传》)诗人围绕一个“怨”字,以明朗而又含蓄的诗句,抒发对屈原其人其事的感怀。
沅、湘是屈原诗篇中常常咏叹的两条江流。《怀沙》中说:“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湘君》中又说:“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诗以沅湘开篇,既是即景起兴,同时也是比喻:沅水湘江,江流有如屈子千年不尽的怨恨。骚人幽怨,好似沅湘深沉的流水。前一句之“不尽”,写怨之绵长,后一句之“何深”,表怨之深重。两句都从“怨”字落笔,形象明朗而包孕深广,错综成文而回环婉曲。李瑛《诗法易简录》认为:“咏古人必能写出古人之神,方不负题。此诗首二句悬空落笔,直将屈子一生忠愤写得至今犹在,发端之妙,已称绝调。”是说得颇有见地的。
然而,屈子为什么怨,怨什么,诗人自己的感情和态度又怎样,诗中并没有和盘托出,而只是描绘了一幅特定的形象的图景,引导读者去思索。江上秋风,枫林摇落,时历千载而三闾庙旁的景色依然如昔,可是,屈子沉江之后,已经无处可以呼唤他的冤魂归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屈原的《九歌》和《招魂》中的名句,诗人抚今追昔,触景生情,借来化用为诗的结句:“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季节是“秋风起”的深秋,时间是“日暮”,景色是“枫树林”,再加上“萧萧”这一象声叠词的运用,更觉幽怨不尽,情伤无限。这种写法,称为“以景结情”或“以景截情”,画面明朗而引人思索,诗意隽永而不晦涩难解,深远的情思含蕴在规定的景色描绘里,使人觉得景物如在目前而余味曲包。试想,前面已经点明了“怨”,此处如果仍以直白出之,而不是将明朗和含蓄结合起来,做到空际传神,让人于言外得之,那将会非常索然寡味。此诗结句,历来得到诗评家的赞誉。《诗法易简录》又赞道:“三、四句但写眼前之景,不复加以品评,格力尤高。凡咏古以写景结,须与其人相肖,方有神致,否则流于宽泛矣。”钟惺《唐诗归》则说:“此诗岂尽三闾,如此一结,便不可测。”施补华《岘佣说诗》评道:“并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种悲凉感慨之气,五绝中此格最高。”无不肯定其意余象外、含蓄悠永之妙。
诗歌,是形象的艺术,也是最富于暗示性和启示力的艺术。明朗而不含蓄,明朗就成了一眼见底的浅水沙滩;含蓄而不明朗,含蓄就成了令人不知所云的有字天书。戴叔伦的《过三闾庙》兼得二者之长,明朗处情景接人,含蓄处又唤起读者的想象鼓翼而飞。
参考资料:
展开阅读全文 ∨
创作背景
三闾庙,是奉祀春秋时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庙宇,根据《清一统志》记载,庙在长沙府湘阴县北六十里(今汨罗县境)。诗人经过此地后,睹物思人,于是写下了这首凭吊诗。
参考资料:
戴叔伦(732—789),唐代诗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常州)人。年轻时师事萧颖士。曾任新城令、东阳令、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晚年上表自请为道士。其诗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但《女耕田行》、《屯田词》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苦。论诗主张“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其诗体裁皆有所涉猎。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将四条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而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册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强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既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神鬼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见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肴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
君休羡,省部选乌台荐。好觑桐江钓叟,万古名传。
自由仙,据胡床闲坐老梅边。彤云变态时舒卷,改尽山川。叹蓝关马不前,
君休羡,八位转朝金殿。恰便似新晴雪霁,流水依然。 梅花
月如牙,早庭前疏影印窗纱。逃禅老笔应难画,别样清佳。据胡床再看咱,
山妻骂:为甚情牵挂?大都来梅花是我,我是梅花。
仙人掌心青数朵,山小乾坤大。不知明月来,且向白云卧,陈抟枕头闲伴我。
飘飘落梅风正冷,缓步苍苔径。一溪流水声,半夜扁舟兴,月明草堂人未醒。
秋风满园三径花,买得闲无价。从前险处行,梦里说着怕,连云栈高骑瘦马。
酒边题扇
华堂舞醄图画展,两行如花面。鹅黄淡舞裙,蝶粉香歌扇,闲搊玉筝罗袖卷。
昭君怨
花间梦乘白玉辇,上马精神倦。哀弹夜月情,别泪春风面,雁归不知多近远。
过刘山
西风小亭黄叶多,鹤领神仙过。云来绿树平,水迸青山破,天然图画添上我。
松江海印精舍
道人不眠中夜起,小立莓苔地。九枝灯上花,四塔庭前桧,梅窗月明清似水。
永嘉泛湖
秋云锦香招画船,一步一个描金扇。花前北海樽,湖上西施面,登楼有谁思惠远?
次必庵赵万户韵
岩扃带云长是掩,不许猿鹤占。《黄庭》尽日观,白发无心染,研朱又将《周易》点。
老王将军
纶巾紫髯风满把,老向辕门下。霜明宝剑花,尘暗银鞍帕,江边草青闲战马。
春情
园林且休题杜宇,未了吟春句。残花酒醒时,芳草人归处,东风小楼听夜雨。
 戴叔伦
戴叔伦 白居易
白居易 曾国藩
曾国藩 左丘明
左丘明 韩愈
韩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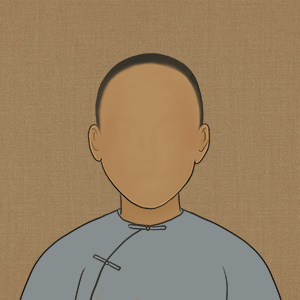 景元启
景元启 张可久
张可久 贯云石
贯云石 晏殊
晏殊 牛希济
牛希济